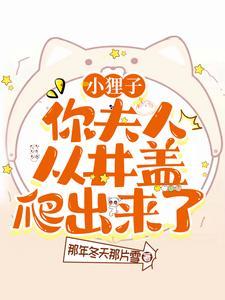少年文学>嫁给病弱太女a后笔趣阁 > 第53章(第1页)
第53章(第1页)
同兴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广陵王太女元祯亲自到淮阴城郊迎接朱大郎,并携带美酒牛羊慰劳他的两百骑卒。
酒酣耳热后,朱大郎见元祯神情谦恭,一直为萧六郎求情,便将戒心全都放下,晚间只带着十多位心腹入城休息。
刚进城一里左右,只听身后爆出了个响雷,连他们**的马都受惊跳了起来。
朱大郎回头一看,淮阴城的闸门猛然落了下来,堵住了进出城的门洞,也截断了他们逃生的退路。
“竖子竟敢欺我!”
悬着的心一下子死了,他目眦欲裂,抽出砍刀劈向元祯的马车。
一时间杀声震天,街边的小贩、买货的行人,都是京口卫假扮的,他们从果子下,布匹中找出隐藏的兵器,与朱大郎等缠斗起来。
上官校尉一杆长枪斜出,拦住朱大郎砍向马车的大刀,接着拍马上前,眼如流星,手腕随眼波一挑,本想用长枪将人的刀卸下,没想到朱大郎喝得烂醉如泥,不仅砍刀脱手飞向路边的屋顶,连人都摔下马匹。
朱大郎摔了一跤,头脑清醒片刻,身子还是软的,他手脚并用笨拙地往后躲,不等挪两步,就被上官校尉一枪戳进心口,在惊惧中结束了性命。
其余人等见大势已去,纷纷放下兵器投降。
“殿下,伪王朱大郎已死。”
车帘掀开,元祯坐在车内,淡淡的扫了眼地上的血腥,沉着道:“割下他的头。”
当夜,梁郡城墙下亮如星点。
五百京口卫与萧六郎的兵马汇合后,每人手中都举起火把,营造出千军万马之势,佯装攻城。
城门守将向下望去,漫山遍野的星火,不知来了多少人,正想向朱大郎报信,几次吊下去的信差都被杀掉,再无人敢去送信。
突然一支长箭射上城楼门柱,上头紧紧裹着个包袱,里头渗出的黑血顺着柱子一滴滴的流。
众将打开一瞧,肝胆欲裂。
里面不是旁人,正是他们的主公朱大郎的人头。
一步卒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将军,将军!城内衙署走水了,白袍军不知从哪钻了出来,正借着火光杀人呢!”
他还未未站稳,一眼认出将领手中的人头,吓得转身就逃,边跑边把兵衣扔下来,自寻个隐蔽的地方逃命去了。
内外夹击,军心大乱,将领们群龙无首,只好另投明主,打开城门迎接萧六郎进城。
天还未亮,元祯就坐到了梁郡的伪王宫里,听上官校尉来报,京口卫的伤亡不过十人,她点点头,教人拿着朱大郎的头,再去劝降其他两郡。
萧六郎、王三娘从宫外进来,他们脱下戎装,见到元祯便深深下拜,感激她的出手援助。
尤其是王三娘,嗫嚅着嘴唇,面上红得像染了鲜血,羞愧难当。
那日她见元祯无发兵之意,便直接掀了桌案,指着人鼻子骂了足足一炷香时辰。
这事要安在其他宗室世家身上,两人早就反目成仇,没想到元祯不仅不计前嫌,亲自屈尊奔波,甚至还以身做饵,设计将朱大郎斩杀。
若按他们原本的计划,合兵强攻,即便能杀死朱大郎,两支军队也剩不了多少人了。
头磕到地上,她背着一根荆条,心悦臣服道:“末将有眼不识泰山,当日多有得罪,还请殿下责罚。”
四轮车的轮子驶到他们面前,元祯亲自扶二人起身,又将王三娘的荆条扔到一旁,宽容的笑笑:“强敌在前,尔等却能重情重义,孤为何要怪罪?”
见她不念旧恶,萧六郎同样拜服,他主动献上白袍军的兵权:“殿下有雄才大略,末将与王三娘商议好了,今后赴汤蹈火,只愿听从殿下一人差遣。”
不出三日,其余两郡看到朱大郎的人头,先后投降。
元祯任萧六郎、王三娘分别为晋陵、梁郡等地太守,暂时打理衮州等地,等她回到南岸,再正式向广陵王为他们请封。
坐上回营寨的船,士卒们说说笑笑,莫不欢欣鼓舞,一是因京口卫首战初捷,士气高昂,二则是为元祯收服两员虎将而高兴。
船只破浪又破风,风刮在人脸上生疼,上官校尉呼出一口白气,见天气冷,就忙转身为元祯搭上件狐裘。
满船的笑脸,连经受过朱大郎折磨的魏十三郎君都微笑着,可元祯的眉宇却带着忧色,托腮怔怔的望着愈行愈远的对岸。
“殿下可是怕萧六郎治理不好衮州?”
元祯摇摇头,将身子全缩进雪白柔软的裘皮里,“他出身官宦世家,又做过一任县令,孤对他们是极放心的。”
那为何还闷闷不乐呢?
上官校尉琢磨琢磨,突然福至心灵,“殿下出来这么久,一定是想念太女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