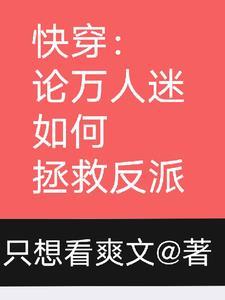少年文学>入戏里缨徽全文免费阅读 > 12求我(第1页)
12求我(第1页)
李崇润瞥了她一眼,脱下外裳。
白蕊忙上前来接,他冷声说:“你出去。”
白蕊担忧地看看缨徽,“喏”了一声,躬身告退。
李崇润仍捏着自己的衣衫。
缨徽接过来,随手丢在一边。
复上前缠着他问今日去了哪里,见过什么人。
李崇润坐在卧榻上,看向铺在地上凌乱褶皱的衣衫,道:“捡起来。”
缨徽只得忍气吞声。
捡起来,将上面沾染的轻尘掸干净。
搭在横杆上。
坐到李崇润身边,握住他的手。
小心翼翼至极。
唯恐推倒两人之间那岌岌可危的支撑。
若是坍塌,万劫不复。
李崇润有心为难她。
为难了之后却并不觉愉悦,反倒梗着一口气。
闷滞而难以纾解。
脖颈间微痒。
他低头,见缨徽伏在了他肩头。
细白的脖颈微微弯着,几缕青丝搔着他。
“七郎,我觉闷得慌,你若是去哪里,带上我吧。”
缨徽扯了个拙劣的谎。
李崇润神色冷冷,凛若寒冰。
一点儿口风都不松。
缨徽蹭了蹭他,撒娇:“总不能一辈子把我关在这里吧。”
李崇润反问:“关你一辈子,又如何?”
他的神情过于严肃,瞧上去不像玩笑。
缨徽悚然。
欣赏着她的惊惧,李崇润终于有了一种扭曲的快感。
他眉梢的冰棱缓缓融化。
唇边噙上浮凉的笑。
缨徽扣紧他的手指,颤声说:“不要。七郎,求你不要。”
她幼时记事起就住在那低矮的芜房里。
十几个小姑娘睡通铺,龟奴看管甚严。
每日的活动范围就在方寸间。
后来回了家,母亲虽为妾室,却极要脸面。
生怕这个曾流落秦楼楚馆的女儿令她蒙羞。
将她关在小小的阁楼里,不许她下楼。
到幽州后,谁都知道她是要给都督做妾。
需得谨守妇德,只能住在那个小院里。
好像她活了十几年,一直在坐牢。
从一个囚笼走向另一个囚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