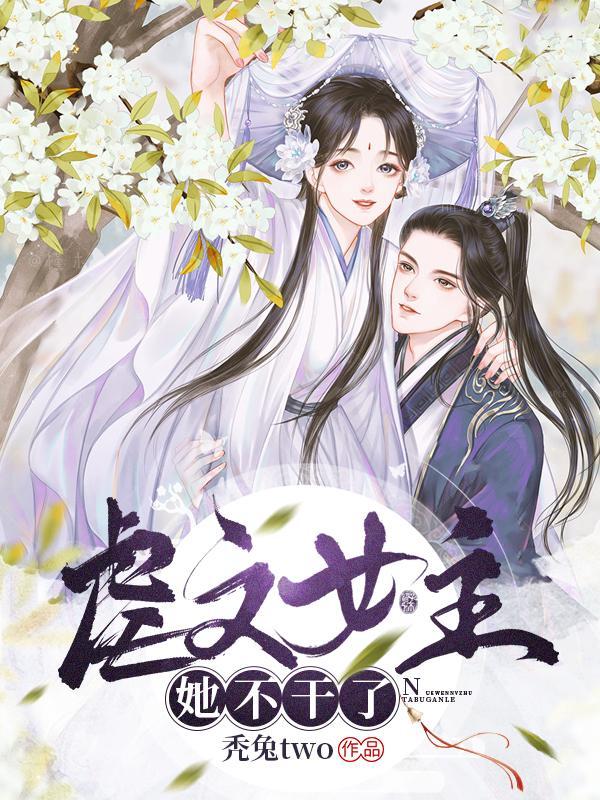少年文学>农家养娃种田日常桃花露格格党 > 130140(第6页)
130140(第6页)
陛下从善如流,殿下就是一流不流。
萧先生抱住阿恒,像哄小孩子一样轻拍他的后背,笑道:“阿恒,我当你答应啦。”
谢恒学着宝儿那样孩子气地嘟嘴,“先生怎么不跟陛下建议让阿年一起来做陪读?”
萧先生:“我就怕陛下也有此意呢。裴家毕竟只是普通人家,没经历过那些阵仗,贸然涉足很容易被人欺负,若是影响了他们本来的发展轨迹,倒是不美。”
谢恒本就说孩子气的话,听先生的意思也很认可。
还是让裴叔好好读书,按部就班参加科举,从科举走出来的家族不管以前多贫寒,也没人敢轻视的。
可若是直接皇恩浩荡,不管本身多纯良正直,也会被人贬损成谄媚之徒。
不好!
萧先生又和小少爷促膝长谈,让他帮自己琢磨一下怎么教导太子那个顽劣孩童。
“为师虽善学问,却不会教顽童,不敢贸然进宫给太子授课,头大得很。”
说到底太子如此顽劣,皇帝要负多半责任。
孩子最会察言观色,感知环境对自己的好坏,若是让他知道自己有任性跋扈的特权,那他只会变本加厉。
这时候就需要严父、严师,可惜陛下因为自己幼年的经历,加之性格宽厚,对这唯一的儿子格外宽和纵容。
皇帝倒是认可近朱者赤的观念,给太子安排学识最渊博的大学士们做老师。
可惜,他怕儿子读书累,八岁才启蒙,还吩咐老师们对太子不要太严厉,不要讲太多书,不要布置太多功课,不要……
刚开蒙那俩月,太子新鲜,也不清楚皇帝和先生们的底线,正经读了几天书,后面一次次试探,发现先生非常宽松,父皇也不严厉,似乎对他读书没有太多要求,那他哪里肯好好读书?
不但不正经读书,还越发顽劣,欺负老师们。
于是学识渊博、人品方正的大学士们不但没能让太子近朱者赤,反而屡屡被他捉弄欺负。
这不,去岁冬天太子殿下又在杨大学士的课上睡觉,还故意打呼噜,把书本上画满打架的小人儿!
他特意把自己画上去,一会儿打漠西可汗,一会儿打海上倭寇,一会儿獠子部跪地向他喊爷爷饶命。
杨学士生气,让他起来罚站,他直接站到桌子上去大喊孤乃大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大将军,要排兵布阵、撒豆成兵!
杨学士让他坐下,看书,他又偷偷爬到桌下,用剪刀剪破老师臀部的裤子,美其名曰让小老师放放风儿!
杨学士被他气得猛灌茶水,频频去净房,他又偷偷跟着老师去净房,偷走老师的裤腰带!
杨大学士被他气得眼冒金星、头也要秃了,提着裤子跟皇帝哭求致仕,要告老还乡!不做官了!
皇帝好说歹说,允许他辞去太子老师的职务才给他安抚住。
而新配的几个小太监,小德子、小顺子、小全子和小才子倒是不错,既能带着殿下玩也能规劝殿下。
可殿下贪玩,只愿意和他们玩,不愿意听规劝,要是劝多了就烦,还要给他们赶回乡下去。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皇帝也有些着急,只得再一次跟萧先生提出请为太子师的意思。
之前大学士们怕萧先生抢他们太子老师的位置,现在他们巴不得萧先生担任主讲师。
杨学士将太子少傅都让出来了!
不干了!
爱咋咋地。
以前萧先生不肯,说自己才疏学浅,不配为太子师,实际是……瞧不上太子,觉得自己教不了顽童,不想自寻烦恼。
现在萧先生为了把弟子留在京城不得不答应教太子读书,因为皇帝拜他为太子少傅,让他亲自为太子安排伴读。
他想让阿恒做太子伴读,如此便不必去苦寒的北地。
即便如此,他也不敢立刻给太子上课,以需要时间亲自考核伴读为由将太子上学的时间延后。
在萧先生看来太子读多少书、有多少学问是次要的,若是他性格坚毅、品性端正、能听得进众臣劝谏,即便学问一般问题也不大,反正政务有朝臣处理,他只需要深谙帝王之术,能熟练平衡朝堂势力加以利用即可。
所以当务之急是纠正太子的心性,让他明白自己是谁,有什么责任,该如何做。
现在的太子骄纵任性,肆意妄为,不肯尊师重道,萧先生觉得贸然给他上课只会自取其辱。
因为第一堂课的成败关系到后面所有课的成败。
若是第一堂课他不能让太子信服、敬重、遵守课堂规矩,那么以后也不必挣扎,只会比杨学士还惨。
这就和猛兽对峙一样,若是不能一击即中反而让对方看出自己的底细,那自己就处于下风,再想赢就是痴心妄想。
他虽然是学识渊博的大人,但太子是顽劣的孩童,不和大人论学识。
从这个角度来看,太子反而有孩子独有的狡猾,有独属于他的跋扈和骄傲,还有压倒一切的尊贵身份。
在太子与老师之间,太子是猎人,老师是猎物,太子是强者,老师是弱者,太子掌控老师,老师还如何引导他?
萧先生知道绝不能给太子掌控自己的机会,不能让太子主导相处模式和走向,必须自己掌控。
所以必须慎之又慎,还不能让太子看出他的慎重和担忧。
因为未知的才是最强大的,一旦让对方确定你的能耐在哪里,那对方就不会畏惧你。
要让太子看不透他的底细,以为他莫测高深,不好拿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