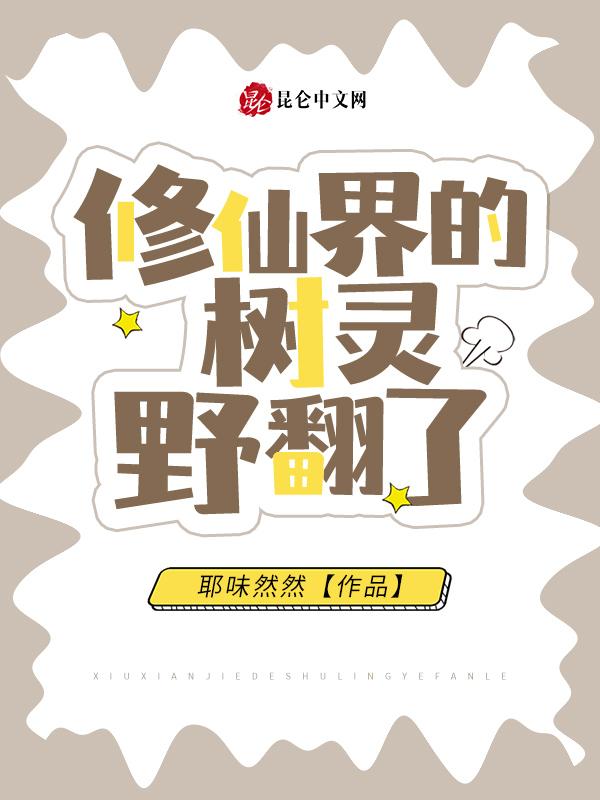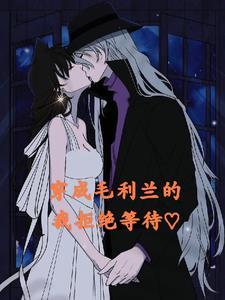少年文学>春季到来绿满窗图片 > 南乡有个小鲁村(第1页)
南乡有个小鲁村(第1页)
南乡有个小鲁村
第二章。去南乡
1。去东北
我大概是两三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去了东北。我父母去的大概是吉林省敦化市。小时候,我爷爷给我起的名字叫吉林,後来又改成银省,後来又被叫成大省。东北野鸡多,野鸡翎子花花绿绿的很好看,我爸爸回山东的时候也带了几根,我爷爷抱着我的时候,还在我的棉帽上插过两支野鸡翎子。
贫苦人家去一趟东北注定是艰难的行程。火车票难买,我们打的站票。印象中很多人一起,人挤人人挨人地站着。我爸爸驮着我,我妈妈背着行李。我爸爸旁边的一个妇女驮着一个小男孩,他手里拿着一个绿色的梨。我手里拿着火烧。我盯着小男孩手里的梨看。那个妇女跟她背上的小男孩儿说:“把你手里的梨给小姑娘吃,行吧?”没等大人同意,我一把抢过了小男孩儿手里的梨,小男孩一把抢过了我手里的火烧。难得有座儿的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吃妈妈从山东带的西瓜子。路上饥渴难耐,有一次火车靠站,我爸爸走下车门,看到一个洗衣服的大姐,他端起那个大姐的洗脸盆子里的水,“咕咚咕咚”就朝肚子里灌下去。
我们坐在火车上,忽而听到大人说:“到山海关了,到山海关了!”我擡头往车窗外头看,外头是苍翠的大山,我看不见哪里有什麽关。我妈妈说:“出了关就是关外了。咱山东属于关里。”
我知道东北不仅有嘉峪关,还有黑龙江,黑龙江里有秃尾巴老李儿。秃尾巴老李儿是一条黑龙。据说黑龙江的命名就是由此而来。妈妈给我讲过秃尾巴老李的故事。说是山东一对姓李的人家,妻子生孩子时,生下了一条黑龙。黑龙一出生就窜到了房梁上,母亲被惊吓而死。父亲拿起镰刀就去砍杀黑龙。黑龙绕梁逃走,仓皇中被父亲砍掉了尾巴。黑龙因为生在李家,又没有尾巴,所以就被叫作“秃尾巴老李儿”。黑龙很有孝心,它知道母亲因它而死,便呼风唤雨为母亲聚起坟茔,盘踞在母亲坟头整整七日,方才离去。黑龙在江中守护过江乡亲们的安全。
这一日,江里又来了一条白龙,它与黑龙争夺地盘,二龙即将展开大战。黑龙托梦给一位员外,让他率领乡亲们准备好窝头和石灰包。在黑龙和白龙决战时,如果江里“轰隆”冒上来一股白水,证明白龙要吃东西补充体力,乡亲们就赶紧往江里扔石灰包,打击白龙。如果江里“轰隆”冒起一股黑水,说明黑龙要补充体力了,乡亲们就赶紧往江中扔窝头。就这样,乡亲们帮助黑龙赢得了大江的主权,此江由此叫做“黑龙江”。乡亲们过江时,只要朝江中高喊“山东人士!山东人士!”过往的船只保准平安无事。
姓宋的很多本家早早就去东北逃荒了,我们就是投奔他们去的。老家人帮我爸爸找了一份刨参土的活儿,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山上的一个小屋里。我爸爸刨参土,天气好的时候,妈妈也带上我跟着。榛子林里有青青的榛子,妈妈去枝头上采来青枝绿叶的榛子,用石头砸开,剥给我吃。妈妈说,人参得用红绳儿绑上,不绑上的话,它会跑的。人参的花朵也是红色的。妈妈找来一根玫红色的毛线绑着。那玫红色的毛线绑着的人参花,一粒粒,红彤彤的,我在梦里都想得到它。
我妈妈说,好的人参是无价之宝。一个男的在外地做买卖的时候,得了一棵老人参,被客店的店家看上了。店家跟他商量,想出钱买他的人参,让他出个价儿。这个男的一时不知道该出多少钱,就躺在他的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他在他的床上滚过来,翻过去,翻滚了半天,还是想不出该出个什麽价儿。这时,店家发话了:“唉,行了,差不多啦。你滚了十八番,我给你十八躺黄金。你看行了吧!”十八躺黄金就是在这个男的刚才躺的地方,铺上十八层黄金。这男的一想,可以了,够多了。他也就同意了。店家把黄金给了他,把那参拿走了。那个男的趁店家不注意,悄悄地又把那棵参拿了回来,用刀子在自己的大腿上划了道口子,把那棵参藏了进去。那参果然是棵宝参,接触了人的血肉以後,竟然让那伤口自己愈合了。那人收好自己从店家那里得来的十八躺黄金,连夜逃之夭夭,奔赴自己的家乡去也。所以说,财宝不能露面,小心被人惦记。
东北的蚊子是大花蚊子,又叫“小咬”,比南方的蚊子咬人厉害。我妈妈说,一个人要是在晚上,在外头待一夜,会被蚊子活活地咬死的。有一个男的,跟人说,他能在外头待一夜。人家不信,就跟他打赌,他如果真地能在外头待一夜,人家就给他多少多少钱。这个男的答应了。人家就把他栓在一棵树上。夜里,来了好多蚊子啊,把他密密麻麻地围住。蚊子喝饱了血,就趴在他身上不动了。他再熬熬,到了天亮,也就赢了。谁知道这个男人的老婆夜里出来上茅房,看到她丈夫被蚊子咬地可怜,就帮他把他身上的那层蚊子打走了。这下可好,刚才喝饱了血的蚊子走了,又来了一批蚊子来咬他。这个男人最後活活地被蚊子给咬死了。
我妈妈还说,有一个女的,嫁给了她的丈夫以後,她的丈夫做了大官。她的丈夫跟她说,你看,你都是沾了我的福气吧。要不然,你哪能当上官太太啊。这个女的说,不是的,是你沾了我的光。我能旺夫。她的丈夫不相信。她就跟她的丈夫说,你要是不信,咱俩就试试,咱俩离婚,你看看,没有我,你还能不能当官。那个男人就跟他老婆离了婚。女人的丈夫动了坏心思,他故意把离了婚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夥夫,让她永世不得擡头。有一天,有一个紧急情报要送。夥夫骑着马去送情报。他在路上饿了,就生火造饭,等他吃完了饭,就把造饭的罐子挂在马肚子上,继续赶路。那马被热罐子烫得生疼,果然快步如飞,夥夫很快就把情报送到了。夥夫因为战功,当了大官,比女人前夫的官还要大。女人又当上了官太太。而女人的前夫也因为干坏事很快就落马了。
我们的小屋在一个山坡上,独门独户,是人家看山的小屋。旁边的地里种了很多北瓜。这种北瓜只有在东北的时候我才听说过它。我在这儿没见过什麽邻居,只见过一个男人,他高高的瘦瘦的,头发蓬蓬的,脸上胡子拉碴。他经常披着件大衣,提着杆鸟枪,满山转悠满地里闯荡。
有一天,他提着枪气冲冲地到了我们家,非说我们摘了他的北瓜。“我的北瓜少了!我昨天才查的,昨天有八个,今天只剩下七个了!是不是你偷的?”他像个野人一样站在我家小屋门前,我看着他,很是害怕。我妈妈从地上提起我家的北瓜,笑嘻嘻地跟他说:“俺没摘你的北瓜。你看看,俺家的北瓜都是俺大娘给的,都好几天了,梗子都老了。你的北瓜是人家才摘的,那梗子还是鲜的吗?”那个野人听了,觉得我妈妈言之有理,才提着鸟枪愤愤地离去。
在东北吃的什麽,我都忘记了。只记得有一天,二叔从敦化来了,带来了一篮子红红的沙果。还有一天,我跟着大人,不知道到了谁家里,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吃糯米丶玉米丶豇豆做的裹着紫苏叶子的“粘耗子”。
我最常去的地方是大刚奶奶家。大奶奶的孙子大刚很是调皮,成天爬树掏家雀儿。他爬到树上,朝树上的家雀扔石头,茅房里蹲着他奶奶,他奶奶知道他又上树了,冲着他就是几声叫骂。
东北有很多向日葵,一大片一大片的。我妈妈跟向日葵叫“迎之葵”。人家种的向日葵收割了,我妈妈去地里捡了人家落下的,炒熟了,留着冬天没事儿的时候,坐在被窝里头嗑。东北的瓜子不叫瓜子,叫“毛嗑儿”。天冷了,父母起来做早饭,我围着被子坐在炕上嗑瓜子。我妈妈给我一个纸盒子,我嗑下来的瓜子皮,吐在纸盒子里。等我起床吃饭的时候,爸妈把我的棉裤拿到火盆上头烘一烘,我就可以穿上热乎乎的棉裤了。
2。南乡有个小鲁村
我爷爷一封家书从中作梗,我爸爸妈妈没办法在东北继续营生,又从东北回到了山东。那时候,我妈妈没几个月就要生孩子了。山东计划生育严格,不宜久留,我爸爸妈妈决定继续出逃,去外地“躲计划”。
我爸爸提议去我大姑家。
我妈妈说:“家军,我去过恁大姐家,恁大姐的老婆婆倒是通情达理的一个人。我跟她处得跟亲娘俩儿一样。恁大姐这个人,怕是不能容纳咱们。再说了,我跟恁娘不和,跟恁大姐也怕是处不好。”
我爸爸满怀信心地说:“没事儿!俺姐能行!”
我妈妈说:“恁姐能留咱吗?你能打包票吗?别到了那里,她再不行。咱还得再回来。”
我爸爸说:“没事儿!我能打包票!”
于是我爸爸拉着板车,板车上,我妈妈抱着我。我们一家三口儿就去了我大姑家。到了我大姑家门口儿,我大姑就坐在她家天井里。我爸爸走到我大姑跟前儿,喊了一声:“大姐!”我妈妈也抱着我从板车上下来,喊了一声儿“大姐!”我大姑耷拉着脸丶愁眉不展。半天,才从嗓子眼儿里慢悠悠地冒出来一句:“嗯,恁来干嘛的?”
我妈妈一看我大姑家里不行,就跟我爸爸商量,不能在我大姑家,得另外找地方。去哪里呢?因为大姨的关系,我们一家三口投奔了南乡小鲁村的梁奶奶家。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被安顿在老杜奶奶家里,住在她家南大门西边的小屋里。从此,我们一家开始了在小鲁村的生活。小鲁村的人提起我们,就说是“躲计划的”。因为梁奶奶管我妈妈叫“三姐”,小鲁村的人也管我妈妈叫“三姐”。
我妈妈为了躲计划生育一直在南乡的小鲁村居住,我爸爸还要回山东种地,不是农忙的时候就来南乡看望我妈妈。我呢,从此开始跟着我爸爸两地奔波丶两处为家。
一间小小的茅草屋,挤下了我们一家三口。靠近西山墙是一张床。床下左手边就是饭桌。此外,我再也记不起来还有什麽家具。一些零碎八务的东西就装在袋子里,挂在墙上的墙橛子上。我爸爸带着我在南乡跟山东之间来来往往。
八月十五的时候,我爸爸给我妈妈买了一块肉。我妈妈把那块肉煮熟了,吊在梁头上。每次吃饭的时候,妈妈就切下一块肉,放在我盛着糊糊的碗里。我就着糊糊吃肉,她啃她自己的煎饼。有一次吃饭,她把这事儿给忘记了,我就看着自己的碗,再看看她。她看看我的眼神儿,突然想起来,她还没有给我切肉,就赶紧去切。等她给我切下一块肉,放在我的碗里以後,我开始喝糊糊,吃肉,她继续吃她的煎饼。那块肉,她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直到长出了绿毛,还在梁头身上吊着,留着给我吃。那种长了毛的熟肉,放在糊糊碗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很好吃。然而那样吃肉的时光也是很少的,我记忆中只有那一快肉。八月十五的时候,我爸爸买来的月饼,我妈妈照例还是留着给我吃的。那几块月饼照例还是留到了长了毛丶生了虫儿,可是,每次,我妈妈拿给我吃的时候,我还是吃得很香。在孩子的眼里,即使是长了毛的月饼,也比那些糊糊丶煎饼好吃。
我吃这些好吃的时候,我妈妈就坐在我对面,吃她的煎饼,喝她碗里的糊糊。她吃地很坚定,也很认真。我看不到她眼里对我还有其他额外的关心。我小时候,理解不了我妈妈的眼神。她的眼神大多数时候是坚定的,是冷峻的。是没有多少传说中该有的慈母的温柔和慈悲的。
直到我痴长到四十岁,直到我自己吃了很多苦,等到我对我的孩子有了一样的眼神儿,我才知道那眼神儿里头的意味儿。那是为了自己的孩儿不挨饿受冻,宁肯受尽耻笑,也要笑呵呵地抄起要饭棍子,挨门傍户地讨饭吃的朱洪武的娘亲的眼神儿。那是准备只身夜闯瑶池,去为自己的官人盗取灵芝仙草的白娘子的眼神儿。那是准备水漫金山,与法海老贼决一死战的白素贞的眼神儿。那是时刻准备冲破大山,去与自己的孩儿相见的三圣母的眼神儿。
梁家三爷爷丶三奶奶对我们很好。我经常跟着爸爸妈妈去他们家玩。他家有一个儿子跟我爸妈差不多大,一个孙子,跟我差不多大。我爸妈带我去他们家,他们吃什麽都会给我吃。有一次,我刚吃完饭,我爸爸带着我去梁三奶奶家,梁三爷爷跟梁三奶奶还在吃饭。我爸爸带着我坐在他们桌子的西南角上,跟他们说话。梁奶奶给我一个菜包子,我伸手就去接。我爸爸立刻训斥我说:“刚吃完饭,又吃!眼馋肚里饱!菜包子!”梁三奶奶笑呵呵地跟我爸爸说:“小孩儿嘛!”
快到晌午了,梁三奶奶做了大米饭。我跟爸爸临走的时候,梁三奶奶给我们盛了满满一大碗大米饭,让我爸爸端回家。我爸爸笑呵呵地端着那碗热乎乎的白白的大米饭,带着我往家走。出了梁三奶奶家,是一条三叉路口儿,路边是人家的篱笆,都用灰黑的枝条围着,那些枝条很高,比我爸爸还要高。我爸爸看看我,停了下来。他走到南边的篱笆旁,掐下两根灰色的枯树枝。他蹲下身来,面朝西蹲着,用那枝条挑起香喷喷的米饭,给我吃。
我们住在老杜奶奶家。老杜奶奶家的老杜爷爷穿着件白背心,他头发花白,眼睛很大,他只有一只手,不太能干活,他的另一只手,据说是年轻的时候因为放炮被炸没了。老杜奶奶的大儿子叫联合,在外地工作,联合的老婆叫葛梅。
葛梅的新房就在我们小屋正南方。娶葛梅的那天,我跟一群小孩子在天井里等着,要看闹新媳妇。葛梅来了,新媳妇到了。鞭炮放起来,鞭炮炸碎的红纸落了一地,闹喜的小青年拿着那些粉色的捆嫁妆的麻绳子,要把新娘子和新郎官儿捆到一起。大人小孩儿,顶着红纸和火药味儿一起往新房里头挤。终于挤进去了。门外头,外庄上一个来喝喜酒的老太太牵着她手里的孩子在骂谁。骂人家光顾着往里挤,把她的孙子给撞倒了,跌破了头,擦破了皮。那孩子顶着一鼻子灰,头上破了皮,在那里自顾自地哭泣,那老太太自顾自地在那里骂着。人太多,谁也不知道是谁挤的。衆人忙着看新媳妇,谁也管不了谁去。大夥儿都到了新房里,新房里,是好闻的刷了红漆的新鲜家具的味道。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知道有什麽甲醛乙醛的,只知道这新的家具就是新鲜丶欢喜。
听说葛梅从小没有爹娘,是她奶奶养大的。老杜奶奶不太喜欢她,老是找她的茬。葛梅怀孕过好几回,都流産了。老杜奶奶二儿子叫运动,是个瘸子,个子很高,胖地流油,不怎麽说话。最小的那个,老杜奶奶就叫他“小三儿”。
有一回,我妈妈带着我在地里拾庄稼,快回家的时候,“小三儿”骑着自行车路过,他看我小,走不动太多路,就主动跟我妈妈说:“三姐,你背着东西多沉,我帮你把大省带回家吧。”我其实跟“小三儿”不熟,我其实是想跟我妈妈一起走回去的。可是我妈妈感念“小三儿”的好意,又嫌我跟着她走回家太累了,她就笑着跟我说:“你先跟恁三叔回家吧,妈妈後头就到。谢谢三兄弟啦!”“小三儿”带着我往家赶。小路的西边,站着一个他认识的小青年儿。“小三儿”要下车跟他说话。他左腿踏着脚蹬子,右腿一扬,从我头上迈了过去。“小三儿”跟那个他认识的人相视一笑。我还坐在他的後座儿上。
老杜奶奶还有一个闺女,经常来看她。一大早,我刚起床,就去了老杜奶奶家里,坐在小板凳上,面向西,看着她们娘儿两个一起吃饭。她们面向东坐着,端起碗吃饭。她们拿筷子夹起一瓣子醋蒜,放在盛玉米糊糊的碗里,“呼啦”喝一口糊糊,把那瓣醋蒜咬掉一半,另一半顺势掉到碗里。然後“呼啦”再喝一口糊糊,把剩下的一半醋蒜吃完。我在一旁看得仔细,她们娘儿两个节奏一致,一样地喝玉米糊糊,一样地吃醋蒜,她们吃得那麽有板有眼。
她们喝糊糊,吃煎饼。老杜奶奶的煎饼不像山东的煎饼,山东的煎饼掺了山芋干子,发黑,发甜,没什麽筋道,倒是显得很松,好咬。南乡人的煎饼是麦煎饼,发白,比山芋干子煎饼筋道,咬起来有些费劲。南乡人吃煎饼,就盐豆子。
“呱啦卷儿,门上槛儿。老雀要吃煎饼卷儿。煎饼卷儿,卷盐豆儿,老雀吃不够。”老杜奶奶常说这句话。南乡人也都知道这句话。我知道这句话,也会说这句话,但是我总觉得那“老雀”说的就是我们。所以,每当老杜奶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不太舒坦,所以我从来不说这句话。也是这句话,让我觉得,这盐豆子离我很远,这南乡的纯小麦的煎饼卷儿离我很远。
葛梅家的新房坐落在我家小屋的正南方。葛梅家西头的石灰地板上,不知道是谁家晒的盐豆子。一笸箩丶一笸箩的,红艳艳的盐豆子,里面是黄黄的煮熟了的咸咸的黄豆粒,外面裹着潮潮的丶红红的辣椒面儿。那红红的辣椒的裹衣在太阳的照晒下,也不再那麽辣丶那麽怕人了。很多盐豆子粘在一起,成了一块一块的。那笸箩不知道是谁家的,反正那麽多,那麽咸,也没有人看管。我跟几个小孩子,拿起一块盐豆子,放到嘴里,尝尝人家的鲜盐豆子。那盐豆子咸咸丶甜甜,干干,是太阳的味道。
盐豆子很好吃,盐豆子卷煎饼也很好吃,但它终究不是山东的味道,不是家乡的味道。这白白的纯小麦的煎饼,像是一卷白纸,无色无味。在这红艳艳的盐豆子,和白白的纸一样的小麦煎饼面前,我就是一只外乡来的夹着尾巴的“老雀”。
我们小屋的右前方是老杜奶奶的小叔子家。我叫他“二老”,就是二爷爷的意思。他家里养着一头驴。他们家的人很温和。他有两个姑娘,大朵丶二朵。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要饭的男人,带着一只小猴子,在他家门口等着,二老转身儿去屋里拿煎饼去了,他家里从屋门口到大门口,扯着一条晾衣裳的钢丝绳。那只小猴子“出溜”一下就爬到了他家晾衣绳上,顺着晾衣绳“出溜”一下,从他家大门口儿爬到他家屋门旁。
大朵丶二朵家的驴,就拴在离我家门前不远的土台子上。天气好的时候,妈妈就找来几个板凳来这里坐着,我们把脑袋放在她的膝盖上,她用火柴棒帮我们掏耳朵。
我自己有时候也来这里转悠。一个有点微凉的早上,我穿着一件紫色带白花的有点破了的外褂儿站在这里。几个不认识的小男孩儿在东边玩。我很想看他们玩,又怕他们笑话我。过了一会儿,他们果然开始笑话我了。“花子!”他们说。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嘲笑我。一天,我站在大街上的黄土台子上玩。人家一家子开着小汽车来探亲。从车里走出来一个男孩子,他冲着我们一群小孩撒糖。小孩子都去抢,就我没抢到。他看了我一眼,冲着我的方向扔了几颗糖。我赶紧去捡。那是一颗黄褐色的糖。很像是後来我看到的太妃糖。
土台子上经常坐着几个小老头儿。我还记得的有严标爷爷,严和爷爷。严标爷爷好像没了老伴儿,吃穿赶不上严和爷爷。严标爷爷俨然是生了病,穿着件发白的淡绿色夹克衫,蹲在地上,病秧秧的,苍白的头发卷曲着,眼睛红红的,眼珠子突出来,时而剧烈地咳嗽两声儿。严和爷爷有严和奶奶伺候,穿得干净一些。他戴着一顶蓝色的帽子,背靠着他家的黄土院墙,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因为生病而变得消瘦的大腿翘在二腿儿上,擡着头跟严标他们说话。严和爷爷的背後是他家的两扇大门。门里是严和奶奶,她穿着蓝色的带大襟的褂子,端着饭碗给她的小孙女蕊蕊喂饭。
大街上,不知道谁家的唱片机里放着歌儿:“正月里正月正,年轻的朋友做事情。做错了事情要法办我的哥们儿呀,做错了事情上法庭了哎嗨哟。”
“手里捧着窝窝头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监狱的生活是多麽痛苦啊,一顿一个窝窝头儿。”
我经常跟蕊蕊一起玩。蕊蕊又聪明,又调皮。我跟她一起玩,被她骂一句丶打两下是常有的事。有一次,蕊蕊去我家里玩,我爸爸切了西瓜,让我们吃。我跟蕊蕊一起捧着西瓜啃。我们都吃得很快,仿佛是在吃西瓜比赛。我的父母就在旁边站着看。蕊蕊吃完一块,我爸爸笑嘻嘻地让她再拿一块。蕊蕊吃完第二块,又去拿第三块。我眼睁睁地看着蕊蕊比我吃地快,抢得比我快。可是,我就是吃不过蕊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