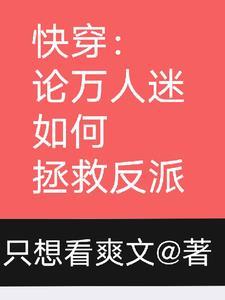少年文学>七零大院职工夫妻无防盗 > 120 番外二(第2页)
120 番外二(第2页)
舒然说不出来话,只能吃力点头。
一转眼,她作为知青下乡快一年了,日常劳动全由大队分配与监督,如今生病住院,自然也是他们来安排後续事宜。
就像护士说的那样,大队的人下午过来了,还带来了一个让舒然意想不到的人。
他虽然站在最後,但舒然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
他五官深邃而俊朗,身形颀长,身姿挺拔精悍,即便置身于高大魁梧的北方人之中也不逊色,反而多了一分冷峻沉稳的气质。
大队来的人具体说了什麽舒然没太在意,只听见一句。
“你之前高烧不退,还一直不醒,我们就想办法通知了你家里人,他听说後,立马请假从海市过来了,现在看到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哎,同志,你怎麽不过来。”
青年从後方走上来,舒然定定的看着他。
她哥的朋友席策远,什麽时候成了她家里人?
男人看出了她的疑惑,不自然的抿了抿嘴,低声问了句:“还难受吗?”
舒然摇摇头。
席策远转头跟大队书记说:“我刚才问了医生,她还得住院观察几天,不然你们先回去,我留在这里照顾她,等她好了我送她回生産队。”
大队书记自然没什麽意见。他们本来以为这个舒同志醒不了了,费大劲联系到她家里人,没想到家人来後她就醒了。
加上她家里人一来就把队里垫付的医药费给了,还要照顾但她出院,也算是给大队省了件麻烦事。
“行,这样也行,不着急回去上工,好全乎了再回队里。”
大队的人走後,剩下席策远和舒然四目相对。
今天之前,他们几乎没有像现在这样面对面看着对方的机会。
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隔着舒羿或是两家父母打个照面,话都说不上几句。
舒然甚至已经忘记,上次跟他说话时是什麽时候。
现在他对她而言,就只是一个眼熟的陌生人。
如今这种状况,她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麽,于是默声低下脑袋。
病房里静得能听见点滴管中的滴答声。
青年的目光从女孩扎着针的枯瘦淤青的手背,游移至她身上穿着的宽大空荡的病号服,到她尖细的下巴,消瘦到凹陷的脸颊,眼窝处的青灰阴影,恹垂的睫羽。
怎麽瘦成这样。
他望着她,呼吸不自觉清浅,尽可能放软语调的解释道:
“知青办的人打电话到厂里,说你病了,但是你哥出差不在厂里,暂时联系不上,我代他过来看看你的情况。”
舒然擡眼看向他,曾经清润盈亮的杏眼此刻一片暗淡,像被浓雾遮蔽的湖面,空洞而静寂。
她的声音虚弱又疲惫,像是一声叹息:“别骗人了。”
这句微弱的话语,重重砸向青年的心脏,他蜷起手指,极力克制着内心翻涌的情绪。
他喉结轻滚,张嘴却被她打断。
舒然看着他,冷静又清醒的说道:“顾彦告诉我,我哥投机倒把坐牢了。”
那天顾彦和她在河边争执,他辩不过她便恼羞成怒的舒羿投机倒把被抓坐牢的事抖出来。
舒然的第一反应当然不愿相信,抓着顾彦要他说清楚,结果被他意外推倒摔坐在河岸边,好在河岸水浅,她自己就能上来,脑子里却还在回想顾彦刚才的话。
怎麽可能呢,她哥明明每个月都有给她写信寄东西,这麽想着,舒然找出之前家里寄来的信件翻看。
爸妈的信越来越短,她哥的信却越写来越长。
这不对。
如果舒羿原谅她了,凭着舒家爸妈爱屋及乌的态度,绝对不会继续生她的气。
爸妈还在生气,说明她哥没有原谅她……
可他不可能不原谅她。
……
只有这些信不是他写的,才能解释两方信件态度差异的原因。
所以顾彦说的是真的,她哥真的出事了。
她本就心情郁结,身体越来越虚,加上思虑过重,受惊又挨冻,当晚烧到四十多度。
要不是她自己强撑着去到卫生所,现在或许已经成了死人,也就不用为难席策远绞尽脑汁的欺骗和隐瞒她。
病房里只剩下舒然虚弱的质问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