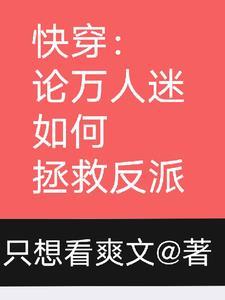少年文学>手中化火失温症候 > 第22章 6(第2页)
第22章 6(第2页)
休整後周艾把何宋明拉起来,才发现他们的吉他手早就不知所踪了,打了个电话累了一串脏话准备投送就听见听筒里传来难以描述的声音,“我草啊宋一洋你不是在石头上吗怎麽滚床上了。”
“宋一洋,你才十八,血气方刚可以,但你有点过分了……你让你男朋友少疼你点行吗?”
听筒的声音朦胧,听起来隔了一段距离。
“挂掉,别理他们,陈弥帆。”宋一洋的声音混沌,“挂掉。”
“要挂掉吗?”
“不要碰这里,陈弥帆!”
何宋明和周艾没人舍得挂断,大大方方开了免提,两人面面相觑,从水火不容变成同仇敌忾,彼此都是对自家吉他手欲求不满的鄙夷。
声音清晰了,不过不是宋一洋:“不劳费心。”
——嘟嘟。
他们不约而同“操”了一声,作为解散的讯号。
何宋明去网吧,这几天他得了空就会去网吧找孟江颐打游戏,孟江颐问他真的有这麽好玩吗?何宋明点头,又说更重要的是他答应了孟江颐要每天基建两小时。孟江颐当时没把那句玩笑话当真,没想到何宋明真的把它当成了承诺。
孟江颐刚给人泡完泡面,熟练地给何宋明开机。
他们乐队三个人,一个人无时无刻不透露出随时赴死的决心,还有一个遇见男友魂会飘,据说分店开业那天陈弥帆也会来,何宋明真怕他一个忘情从台上跳进他对象怀里了。这样想,还是孟江颐好,性格最好,脸也最好。
他跟发小斐合说自己在茉城认识了个能当电影演员的人,偷拍了一张有些模糊的照片给斐合看,见惯莺莺燕燕的斐合也忍不住夸赞。他昨晚就做了一出像电影似的梦,孟江颐靠在公交车的扶手上,摇晃的车厢带动他漂亮笔挺的身体,白皙的手臂变成垂吊的铃兰,乌黑的瞳孔里望着他,耳边是小河流淌,粉紫色的野花飞舞,不过在孟江颐开口说台词前的一刹那梦就结束了,醒来只记得下了公交站在飞舞野花中不会被吹走的孟江颐,那一刻何宋明很希望有什麽东西能够把这个人带走。
何宋明上机继续建设他和孟江颐的世界,不一会孟江颐也连进来,起初只有几个方块大的木屋摇身一变成了三楼高的小别野,就建在河畔,石墙围住的院子里种着翠绿的西瓜和橙黄的南瓜,尽可能地复刻了他们住的那栋房子。
何宋明用孟江颐钓到的鱼驯服了一只美短起司猫,落日悬挂在河岸尽头,孟江颐的视角停在二楼的阳台望下凝视着垂钓的何宋明以及角色身边的猫咪,心湖翻动,想一百九十天也会很快过去。
不知道几轮日落西沉,反正最後两人躺在黑暗的房间里退出了游戏,行入真正的夜晚穿过大街小巷回家,何宋明嘀嘀咕咕地说酒吧周末就要开业了,问孟江颐要不要来看他们演出。不看的话以後可能就看不到了。最後一句话他没说出口,替换成还可以带小澄姐姐一起来。孟江颐说好。
钥匙转入锁孔的时候何宋明问为什麽最近孟江颐都不跳房子回去了,孟江颐开门进去,声音从黑暗里传来:“以前只有一个人,开门声音心慌。”
意思是现在不一样了,代表不一样的本人愣了一秒随後跟上去,心里不可名状的哀伤,他走後孟江颐还要经受多久这样的心慌?
有那麽一瞬间他不想走了,孟江颐洗澡的时候,何宋明终于难以按捺冲动,跑到一楼给何白珍打电话,他很少主动联系何白珍,何宋明算了算时间问妈妈吃过饭了吗。何白珍大概也没想到会接到何宋明电话,顿了下才说吃过了。
“你们大概都知道了吧,我在茉城,离原渝都一东一西的,学校的项目我也有远程跟进,没全忘,暑期的项目要结束了,”他语无伦次地铺垫了一通,最後才犹犹豫豫问:“妈,我有没有可能留在?”
“何宋明。”何白珍念他的名字,何宋明心惊了一下,提前知道答案:“你疯了吗?你在茉城玩疯了吗?”
何白珍咳嗽了一声:“这个关头给你两个月已经很多了。”
什麽关头?他不是一生都在这一个关头吗,只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关头。既然说是关头,那总要有另外的时间可能性和机会吧,在哪里呢?他没问出口。
“九月前必须回来,知道了吗?何宋明,必须回来。”
何宋明失魂落魄地回到孟江颐的房间,孟江颐已经出来一会,擡头看他,他解释道:“去倒水了。”
孟江颐嗯了声,说水热好了可以洗了。何宋明抱着衣服进去,蓬头的水柱冲刷着他的发顶,流到耳廓,疼得他龇牙,头发不知不觉变得干枯,颜色也淡掉很多,关了蓬头何宋明用毛巾粗暴地揉了揉自己的脸,一双眼睛有点红,好在孟江颐在做自己的事没有看他。
何宋明吹头发的时候在想第二天要去买碘伏消毒,这麽多个孔要是养不好得多遭殃,他小心翼翼地吹着头发,吹干刚把电风吹放下,一只手忽然拢住了他的发丝,棉签沾着冰凉凉的百多邦擦拭过创口。
“回来路过药店,给你买了消毒的东西。夏天更容易发炎,穿孔师让你注意点,前两天别淋水,果然没听话,敢一口气打这麽多个的只有後羿了。”
孟江颐手指点过九个银色的圆珠,像拨弄了九个太阳。指腹和耳朵都变得灼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