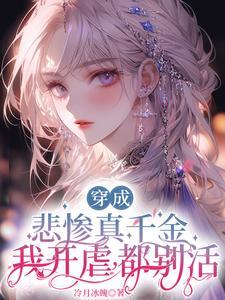少年文学>我在妇科当医生的日子 > 第999章 岁月终究无情(第1页)
第999章 岁月终究无情(第1页)
当长安城的柳絮开始纷飞时,李三娘他们准备返回长安的行装也已准备妥当。
在南地他们呆了已有五年了。
此地气候湿热,南地的妇人,因常年劳作于湿热环境,多患带下之疾(妇科病),产后感染也远比北方频繁。
此外,小儿疳积(脾胃受损,饮食异常)、暑湿之症更是常见。
(暑湿证,中医病证名。指暑湿之邪交阻内蕴所致的,以口渴、神疲倦怠、肢体困重、关节酸痛、心烦面垢、汗出不彻,舌红苔黄腻,脉滑数等位常见症的证候。)
李三娘带着妇产堂的女医们,白日看诊,夜晚则与众女医一起研讨病例,将从长安妇产堂中带来的医术与南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调整药方,制定更适合当地的诊疗规范和卫生条例。
她强调水源清洁、食物煮沸,推广艾草熏蒸以驱蚊防病,并将这些预防理念编成通俗易懂的歌谣,让女医们教给当地的妇人。
跟随李三娘一起来到南地的露珠儿就充分挥了她自己的长处,她将妇产堂的账目、药材进出打理得井井有条;
还协助跟随她而来的唐大郎,在广州府建立了与当地药商、以及更远的南地的药材补给线。
唐大郎他还跟着当地人学习辨识南地特有的药材,丰富他的药学见识。
这五年里,露珠儿与唐大郎在异乡相互扶持,感情愈深厚。
在他们来到广州府的第二年,于一个木棉花开得如火如荼的春日,露珠儿她顺利诞下了一个女婴。
是李三娘亲自接生的。
产房内,露珠儿她表现出了乎寻常的坚韧,她牢记李三娘平日的教导,调整呼吸,配合用力。
李三娘握着露珠儿的手,沉稳的出指令,她的眼神里既有母亲的疼惜,更有医者的专注。
当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划破南地湿润的空气时,院里院外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出来。
“是个俊俏的小娘子,”李三娘将清理干净的婴孩抱到了露珠儿面前,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你看,她多像你小时候啊。”
露珠儿疲惫却幸福的笑了,她轻轻碰了碰小小女婴那粉嫩的脸颊。
因生于南地,又恰逢蛾眉月之夜,这个孩子的小名就叫“月牙”了。
而孩子的大名,则是露珠儿和唐大郎邀请李三娘给取的,李三娘思来想去数日之久,最后,才给小月牙起了名字——唐雯君。
“阿婆愿你德才兼备,做一个有坚韧风骨的人!”
日子,就如流水一般。
自李三娘到此后,就与早就在此地多年的钟离文莲一起,联合当地官署,不仅仅把此地的妇产堂好好整顿了一番,还在此地又开了一家“平安女医学院”的分院。
南地终归就还是离着长安太远了些,长安的女医学校虽然每年都能培养出百多位女医来,但对国土辽阔的大唐来说,仍旧就还是杯水车薪了些。
所以,李三娘她就觉得,这当地的问题,就还是要在当地解决才好。
跟随李三娘来到南地的女医们,如此就要辛苦些,身兼数职来了;
她们既要在妇产堂当值,还得去女医学院做先生,这还不算完;
李三娘就还定下了如长安太医署那般的,每季度去往乡村义诊的事。
这五年里,李三娘带着妇产堂的女医们,上山下乡的,她们的足迹遍布岭南各州府,建立的妇产堂分堂的网络愈稳固,培养的本地女医也开始崭露头角。
另外,李三娘她编纂的《南地妇人小儿常见疾患应对手册》也被刊印放,惠及此地的更多医者。
如此,哪怕就是过了五年,也不过才在南地给当地的妇产医疗体系搭了个骨架出来而已。
但李三娘她觉得南地的妇产医疗体系就也算是步入正轨,是能够自行良好运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