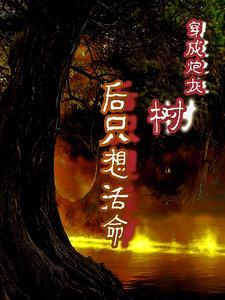少年文学>月失行而南 > 变与不变(第2页)
变与不变(第2页)
“对不起……念念,对不起……”
“是我太自以为是了…我怎麽会以为,不告诉你……才是对你好……”
她的话语断断续续,被压抑许久的情绪如同决堤。
曾几何时,她可以坦然地对陶念说“去做你想做的”,那份底气源于对自身价值的确认。
那时的她,站在讲台上能掌控全场,在职场中游刃有馀,那份从容,让她给得起陶念最大的自由和尊重。
可如今,当简历石沉大海,当“36岁”这个数字在屏幕上反复刺痛她的眼睛,一种深层的丶她从未体验过的惶恐,正悄悄击毁着那份从容。
她开始在意陶念加班的时间是不是变长了,会在对方挂断电话前下意识地问“你几点回来”,甚至会在陶念兴致勃勃地谈论工作新进展时,感到一丝难以啓齿的落寞。
她不再是那个能轻松说出“你尽管飞,累了就回来”的林知韫了。
此刻的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从身边这个唯一的光源身上,汲取更多的温暖和确认。
这份不自觉的依赖和患得患失,连她自己都感到陌生,却又无力阻止。
***
接下来的日子,两个人各自奋斗着。
陶念的工作迅速步入正轨,辅导员的工作琐碎却充满挑战,她每天带着新的见闻和小小的成就感回家,像一棵努力扎根抽枝的树,生机勃勃。
而林知韫的生活则陷入了缓慢的停滞。
她投递简历,然後等待。从最初的期待,再到近乎麻木的重复。回复寥寥无几,即便有,也常是被婉转拒绝。
白天,她在公寓里翻阅招聘信息;傍晚,她听着陶念的开门声,便关掉了电脑。
她开始睡得很多,仿佛睡眠是抵御焦虑和虚无的唯一武器。
一种微妙的变化,在无声无息中发生。
不激烈,不争吵,却像水渗入沙地,缓慢而坚定地改变着一些什麽。
她们依旧交谈,陶念分享学生活动的策划丶棘手的个案处理丶职业发展的新可能。林知韫能提供的,更多是过来人的经验与宽慰,却少了那份源自共同战场丶势均力敌的共鸣。
曾几何时,她们是并肩作战的同事,是能就一个教案丶一项政策深入探讨的同行者。
她们理解彼此工作的具体问题与烦恼,那种默契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
现在,陶念在上升的轨道上加速行驶,视野也变得不断开阔。
她清晰地感觉到,某种平衡正在被打破。
她依然是年长的那一个,却似乎不再是那个能稳稳托住对方丶提供指引和依靠的人了。
晚上,陶念给陆瑾年打去了视频通话。
屏幕那头的陆瑾年听了陶念的叙述,轻轻推了推眼镜,给出了具体的评价:“林老师这种情况,确实不容易。她在晋州教育系统工作十多年了,积累的人脉丶资历乃至那种从容,都是基于那个平台。现在来到锦城,等于放弃了之前的根基,一切从头开始。这个年纪,在二线城市,高不成低不就是常态。好的管理岗倾向本地熟手,基础岗位又嫌她资历过高。学历在一线城市是硬通货,在这里,有时反而不如本地关系网实用。”
陆瑾年顿了顿,语气里带着理解:“她当初选择离开,为你放弃的,远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多。这种落差感,需要时间消化。”
挂了电话,陶念的心情有些沉重。
而另一边的林知韫,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与挣扎後,也逐渐转变了心态。
她开始降低标准,将简历投向了几家大型教培机构,甚至开始关注线上教育课程开发的岗位。
“无论如何,先有一份收入,站稳脚跟再说。”她这样告诉自己。
一天早上,林知韫的手机屏幕亮起,一封新邮件提示跳了出来。她原本以为是某个教培机构的自动回复,随手点开,却怔住了。
发件人是锦城市外国语学校,邮件正文礼貌地邀请她于下周前往参加初中部课程研发岗的面试。
这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锦城外校是本市老牌重点,以教学严谨和资源雄厚着称,她当初认为希望渺茫,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递的。
“怎麽了?”陶念端着水杯走过来,察觉到她的异样。
林知韫把手机屏幕转向她:“是锦城外国语学校的面试通知……”
“太好了!”陶念立刻放下水杯,脸上绽开笑容,比她自己收到offer还开心。她握住林知韫的手,“下周一我调休,陪你一起去!我得去见识一下林老师在面试考场上的风采。”
***
锦城市外国语学校的行政楼走廊空旷而安静,林知韫坐在门外的椅子上,其他的应试者明显是应届生,眼里有一种不谙世事的清澈,自己置身其中,总有些格格不入。
“下一位,6号。”会议室的门口探出一张年轻的面孔。
她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外套的下摆,迈步走了进去。
椭圆形的会议桌後坐着三位面试官,中间是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丶神情严肃的中年男子,应该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左边是位面容姣好但眼神略显挑剔的中年女性;右边则是一位较为年轻的男性,一直低头翻看着她的材料。
“请坐。”副校长擡手示意,语气平淡。
面试的前半程进行得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