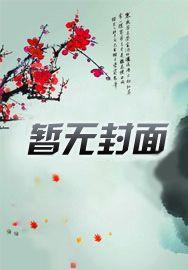少年文学>我靠菜谱 > 第440章 她不拜灶灶却拜了她(第1页)
第440章 她不拜灶灶却拜了她(第1页)
晨雾未散,拾烬村外忽现百人长队,皆捧粗陶碗,跪伏道旁。
霜气凝在梢眉间,却无人起身拂拭。
为老妪枯手捧着一只缺口的旧碗,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声音颤抖如风中残烛:“求苏娘子赐一碗‘回甜粥’……救我儿哑舌之症!”
她儿子跪在身后,嘴唇干裂,喉结上下滚动,却不出一丝声响。
那是三年前“禁火令”时被烙铁封喉的孩子,从此再不能尝滋味、诉悲苦。
萧决眉头一拧,玄氅翻卷,抬步欲上前驱散人群。
他深知此时苏晏清已油尽灯枯——七日不语,五感渐闭,连呼吸都靠地脉牵引,如何还能应这千人所求?
可刚踏出一步,肩头却被一只粗糙的手按住。
是火余娘。
那渔妇披着补丁摞补丁的麻衣,眼神却亮得惊人:“大人,他们不是来求饭的。”她顿了顿,嗓音低沉如灶底余烬,“是来寻‘心安’的。”
萧决脚步微滞。
他知道这两种渴求截然不同。前者为生,后者为魂。
而此刻,百姓所求,正是那曾被律法碾碎、被恐惧掩埋的——人心本味。
风掠过荒原,吹动苏晏清鬓边碎。
她目光空茫,瞳孔里映不出人脸,也照不见悲欢。
可当最近那只冷粥靠近,她竟缓缓抬手,指尖轻触碗沿。
刹那间,异象顿生。
碗中乳白米汤微颤,浮油如活物般游走,自流转成“三起三落”之纹——那是野灶古法中最难掌控的火候痕迹,全凭厨师心意与锅气共振而成,三十年前已被列为“乱火邪术”。
老妪怔住。
她不懂这些规矩,但她记得——这纹路,像极了出嫁那年,母亲在灶前为她煮的那碗糖心蛋花粥。
她颤抖着啜饮一口。
下一瞬,泪水奔涌而出,整个人伏地嚎啕大哭:“甜了……甜了啊!像我出嫁那天,娘喂我的第一口……我以为这辈子再也喝不到了……”
哭声撕开晨雾,惊起一群寒鸦。
其余百姓纷纷低头看向自己手中冷粥,有人试探着抿了一口,忽然浑身一震;有人将粥倒入孩子口中,那原本木然的小脸竟微微动容,喃喃吐出一个字:“暖……”
烟记吏跪坐一旁,炭笔疾书,竹简噼啪作响:“壬寅年腊三十,百人请粥,一触即化,油自成纹,谓之‘心启纹’。”笔尖忽顿,他猛地抬头——
东方天际,传来悠远钟声。
三十六名黑衣执典者列阵而来,足踏黄沙,步伐齐整如刀裁。
为青年身披铁灰袍,手持鎏金铁卷,眉目冷峻,步至村口戛然止步。
梁守名。
《新灶典》执,梁续火之子,执掌九城灶务的年轻祭司。
他目光扫过满地残灶、百姓手中粗碗,眼中闪过一丝痛惜与怒意,随即朗声开口:
“奉《新灶典》律令:苏氏一门,唯传一道,万味归宗。自此,非苏氏亲授之味,皆为伪味;凡私设野灶、妄调火候者,焚灶断火,永不得复燃!”
话音落下,随从执火钳者已上前,欲砸毁村民临时搭起的土灶。
然而就在此刻,梁守名抬眼望见风沙中的苏晏清。
她倚在萧决身侧,衣衫破旧,丝凌乱,唇色苍白如纸,唯有那只攥着“灶灰粮”的手,仍蜷得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