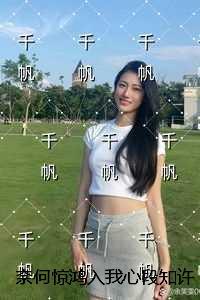少年文学>一挽长发定终身gl > 第56章 纸鸢 君向浩渺逍遥处自在缱缱掌控中(第3页)
第56章 纸鸢 君向浩渺逍遥处自在缱缱掌控中(第3页)
什麽鬼风俗也不是,陈良玉心里生出些微的低落情绪。
怎麽能不是呢?
刻簪子这麽无聊的事情都能成为风俗。
风筝线也行。
陈良玉身上时常备着针线,舞刀弄枪衣料破了随时补两针。锦缎表面光滑,打上结也很容易开,不用人解,走两步就散了。
她将线绕开,穿针在谢文珺打的结上横针竖线地缝合,将帕子缝死在腰带上,“你去南境时给我个信儿,祺王暂时不会举全力攻过来,他定会先派先锋军试探临夏的兵力,解决完他们的前军我便能腾出手。就算快马急奔,我从前线赶到南境陆平侯府也要一日,你身边虽有荣隽,庆阁与赵明钦手中也有人马,可衡继南毕竟在南境统兵许多年,在军中威望尚存,千万要知进退,别把人逼急了。”
“我有点乱。”
“你先别乱,不是乱的时候。另立新帝这麽大的事都没从你嘴里透出一丁点风声,你不是遇到事就会心乱的人。”陈良玉打了个线结,针线收回布包里,擡头看,恰见谢文珺眼眸中一片清辉向明月。
“你这麽看着我干什麽?”
她还想说些什麽,话到嘴边猛然想起,上一次她问出这句话时,接下来便发生了些令她昏头的事情。
脸颊轻微燥热,幸而路过的清风拂过面颊,带走了那丝不易察觉的悸动。
陈良玉道:“我该走了。”
谢文珺道:“你万事当心,此间诸事有我。”
“珍重身体。”
陈良玉只身向垂花门外走去,日晖将她的轮廓勾勒得不太真实,蓝墨色的衣袍鼓动丶消失在门外。
不久,马群嘶鸣丶奔腾,只馀高墙下回荡着渐行渐远的马蹄声。
谢文珺:“荣隽。”
荣隽从垂花门外露头,“臣在。”
“新帝即位,喜获明珠,双喜临门,去请临夏的各位大人来王府喝喝茶。”
荣隽:“全部都请来?”
“凡七品以上的,都请来。”
谷燮道:“临夏留在城中的尽是文官之流,让行谦代荣大人去各位大人府上跑一趟就是。”
“眼下风声鹤唳,都怕这趟来了王府有去无回,能推拒的,那帮人定然找借口不来,陈行谦一副文弱书生模样镇不住场面,荣隽忙完这遭,有的是其他州丶郡的人等他去请。”
谢文珺转身对荣隽道:“好好地请来,少动粗,礼便不必备了,免得日後背地里非议本宫借机讹诈他们钱财。”
荣隽:“是。”
暖阁点了一炉安神香,内厢房血腥气重,荀淑衡被移来暖阁休养,还睡着,朱影每隔一炷香的时辰便号次脉。又一次探过脉搏後,把荀淑衡的手放回锦被,“脉象已经平稳了。”
谢文珺坐在堂下,双手轻轻搭在座椅的扶手上,道:“有功当赏,你想要什麽赏赐?”
朱影却没说要什麽赏赐,眼神囧囧,在谢文珺脸上转了一圈,“你这身子骨不宜操劳过甚,做个游闲之人,好好养着,也能长命百岁。”
“多谢提醒。”
“我很奇怪,帝王血亲,脉象上怎麽会有离魂引的迹象?长公主殿下。”
原来东胤那害人的秘术名为离魂引。
谢文珺道:“运气不好,替人还了冤债。”
“这离魂引呢,是东胤尤家始创,专为达官显贵养死士的,尤家本也是行医世家,後来做官去了,东胤那二世祖皇帝突然暴毙,旁系皇亲夺了皇位,很难说跟尤家有没有关系,只知t道尤家很得新皇赏识。待上一代人死得差不多了,尤家後人突然就长出了良心,把这害人不浅的东西自行毁了。”
“我很小的时候,梁溪城经常丢孩子,我还见过离魂引的死士,应该是个没养成的,不过也没人样儿了,像是从哪里逃出来的,到处抢吃的丶伤人,被抓住打到半死。我爹想救他,便带他回山庄医治,他醒了竟差点剜了我爹的喉咙,最後还是没救活。”
朱影移来一柄鹤顶长足油灯,鹤的腹部便是添灯油的油壶,“人呢,像这油壶里的灯油,需插上灯芯慢慢地燃,离魂引是在油壶里点火,很快便烧尽了,想续命只能靠药吊着。外物终究不及五内,你症状虽轻,但它就像是一簇火种,不留神便会烧起来。”
谢文珺没被她唬住,付之一笑,道:“本宫好得很。”
“不见得。”
黛青:“大胆!”
朱影:“我好意提醒,不识趣便罢了,懒得管。床上那位没事了,按方子服药,多养些时候,这里若没有其他病人,在下告辞。”
作者有话说:谢谢看到这里的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