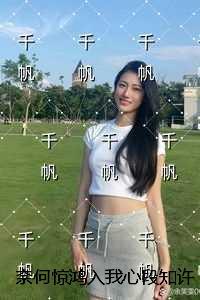少年文学>予你醉眠 > 第43章 他的兰嘉 在他的臂弯安眠(第2页)
第43章 他的兰嘉 在他的臂弯安眠(第2页)
孟岑筠也听在耳朵里,留了心,倒觉得她这话里有双重意思。
是在怨他将兰嘉带走了不回来?还是在恨他让她享受不了天伦之乐?
他也莫名地升起一股怨气。
兰嘉不在身边了,她可以种种花,养养猫,随时随地找人来解解腻,逗闷子,走了一个乔子穆,要搜罗来各式各样的,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兰嘉,她照样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可他不行,这些年守着这一个目标过惯了,他简直不知道没她的日子要怎样过活。为什麽偏要同他争抢?明明这天底下没有人比他更需要她!他在暗地里紧咬着腮帮子,浓浓的怨恨直堆上来,仿佛所有人都要来抢走他唯一的心爱。
再怎麽谈判与施压,纵使不要脸面又如何?他不会轻易放手。
孟岑筠紧绷着脸,看向紫檀木牌匾上的莲轩二字,一阶一阶地走上去。
推开门,正前方,罗汉榻上坐着的老太太推了推眼镜,亲昵笑道:“小岑,来啦?”
仿佛什麽都没有发生过的态度,孟岑筠心里有点异样。
他仍维持着面上的恭敬,应了声,径自找了把圆背交椅坐下。
老太太吩咐佣人上茶来,便低下头去顾自己的事了,空气里冷清清,像是故意晾着他。
孟岑筠只好等着,擡眼打量周围,四四方方的屋子,摆件不多,却也古朴考究,一张罗汉床安置在窗边,几扇冰裂纹的梅花窗对开了一扇,那外面是荷池,夏夜里偶尔传来几声蛙鸣。
窗外荷风阵阵,暖意轻薄的灯光下,老太太腿上平摊着一本厚厚的大相册,正挨页翻着,像是在找什麽。
佣人进来了,将两盏茶搁在各自的小几上。
孟岑筠揭开盖子,天青釉的瓷杯里漂浮着小菊花,花朵洁白,花蒂青绿,在热水中胀大了,袅袅浮出清苦气味。
“闲来无事种了些白菊,去年收了一小片晒干,晚上不宜饮浓茶,正好泡一些。”
孟岑筠点头,低头抿了口。
老太太看他一眼,又道:“园子里来了几株花手鞠绣球,我准备亲自移栽,小岑,不如你小住几日,帮着我一起修修剪剪,如何?”
这是有意困住他?不让他与兰嘉接触?孟岑筠没作声。
“许久未见你登门了,这次来,想必也满腹疑问,不如趁着这几天,我向你一一解答?”
她果然知道些什麽。
又想到自己本就是为求证来的,孟岑筠这才应下了。
孟岑筠起身接过,认真端详着那张照片。
背景像是圣诞节,派对上,楼梯立柱上系着雪松花环与大红蝴蝶结。一男一女并肩站在楼梯口,西服与白裙,很亲昵地各抱一只胖猫咪。看相片上显印出来的时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他几乎立刻就认出来了。
那两人是年轻时的孟士渊与易含真。
医院内,兰嘉小腿抽动,忽然惊醒了。
不过小憩一会儿,竟然做噩梦,她还是无法克服待在医院的不适感。
肩颈痛,兰嘉伸手捏了捏,发现自己刚才一直靠在人家身上。
“抱歉!”她弹跳似的坐直身子。
宋青渠微笑着摇摇头,示意无碍。
又看了眼时间,喃喃道:“已经这麽晚了。”
正巧这时门开了,两个护士推着转运床出来。
兰嘉急匆匆地站起身,凑上前去关注着。徐心文已经醒了,一张脸苍白浮肿,能看出吃了不少苦头。
她鼻子没来由的一酸,高兴她平安,也心疼她。
两人视线对上了,徐心文扯扯嘴角,很没力气地对她说:“去替我看看……孩子,可以吗?”
兰嘉点点头。
护士要将徐心文转入病房,才做完手术,担心她独自过夜,兰嘉让宋青渠去护士站咨询请护工事宜,自己则去到同楼层的NICU。
到小窗口说明来意,又登了记,兰嘉才被放进去。
里面是一溜的单独小隔间,做了一面透明的玻璃窗,方便家属探视。挨个挨个找过去,终于找到徐心文的女儿。
兰嘉趴在玻璃上抻着脑袋看,保温箱里的婴儿经过一番照料,已经熟睡了。
她看到她细细的脚腕上系着白腕带,因为还没名字,所以写的是母亲姓名。
早産下来,那麽小,红扑扑的,皮肤嫩薄得近乎透明,像不足月的可怜猫崽。
小孩子的降生太不容易,是母亲拼了命才有的。
兰嘉不由得想到已经过世的易女士。
她当时也是拼了命才生下她的。
兰嘉手心贴在玻璃上,睁着水汪汪的两只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里面。
她全然没察觉,不远处立着的一个高大黑影,正用一种野兽蛰伏的眼神,紧密盯视着她。
作者有话说:和妹妹分开後,哥整天的内心Os:兰嘉,兰嘉,兰嘉,兰嘉,兰嘉,兰嘉,我的兰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