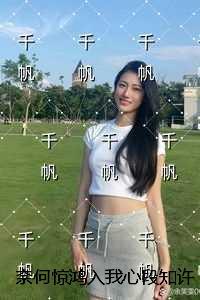少年文学>骶神经的作用功效 > 第75章 烈火与决断(第1页)
第75章 烈火与决断(第1页)
柳玉茹寄来的那张支票影印件,如同在她心湖里投下的一块巨石,表面的冰层被砸得粉碎,底下汹涌的暗流与沉积的泥沙疯狂翻搅。那行「他当年可是毫不犹豫」的附言,像淬了剧毒的冰锥,反复刺穿着她试图用理智构建的防御工事。尽管江辰的证据链清晰,尽管她理解那背后的凶险与无奈,但亲眼目睹这铁证,感受着那字里行间透出的、来自三年前的冰冷决绝,苏晚晚依旧无法平息内心那滔天的巨浪。
委屈,愤怒,被背叛的刺痛,以及一种深沉的、连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失望,在她胸腔里冲撞、酵,几乎要将她撕裂。她把自己关在临时书房里,对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一动不动地坐了许久,直到指尖冰凉,直到初升的晨曦为天际染上一抹凄冷的鱼肚白。
新的一天,依旧要面对病床上那个男人,依旧要维持着那摇摇欲坠的专业与冷静。
她走进顾砚辞的病房时,脸上看不出任何异样。依旧是那副清冷的表情,依旧是精准利落的操作。测量体温,检查伤口,调整输液,每一个步骤都无可挑剔。
顾砚辞醒着,靠在床头。他的脸色依旧苍白,但眼神比前几日清明了许多。他看着她,敏锐地察觉到她今天的气息有些不同。虽然她极力掩饰,但那过于刻板的动作,那刻意避开他视线的眼眸,以及那周身散出的、比往日更加凛冽的寒意,都像无声的警报,在他心中拉响。
他试图开口,想询问念念,或者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集团事务,试图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
“念念昨晚睡得好吗?”
“嗯。”苏晚晚头也不抬,专注于调整监护仪的参数。
“江辰说,城南那边……”
“医疗期间,尽量少操心这些。”她打断他,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疏离。
顾砚辞所有的话都被堵了回去。他看着她在房间里忙碌的身影,那背影挺直,却仿佛背负着无形的千钧重担。一种无力感深深攫住了他。他宁愿她像之前那样与他激烈争吵,也好过现在这样,将他彻底隔绝在一座无形的冰墙之外。
他不知道的是,那堵冰墙之内,正有烈焰焚城。
完成上午必要的护理,苏晚晚一刻也未多留,转身便走。就在她的手触碰到门把手的瞬间,顾砚辞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近乎恳求的意味:
“晚晚……”
这个名字,他许久未曾这样唤她。
苏晚晚的背影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握住门把的手微微收紧。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回应,只是停顿了那么一秒,便毫不犹豫地拧开门,走了出去。
“砰。”
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也仿佛关上了最后一丝沟通的可能。
顾砚辞望着那扇紧闭的门,眼底最后一点微光,也渐渐黯淡下去。他缓缓闭上眼,浓密的睫毛在苍白的脸上投下脆弱的阴影,胸腔里弥漫开一片荒芜的空洞。
苏晚晚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径直去了顾砚辞的书房。
她知道他这里有一个壁炉,虽然平日里更多是装饰作用。她反手锁上门,走到壁炉前。清晨的室内有些清冷,壁炉里空空如也。
她站在那里,从口袋里缓缓掏出那个白色的信封,抽出里面那张薄薄的、却重若千钧的支票影印件。
纸张在她指尖微微颤抖。
柳玉茹想看到什么?想看到她崩溃?看到她拿着这张纸去和顾砚辞大吵大闹,彻底决裂?想让她被过去的阴影吞噬,变得疑神疑鬼,再也无法与他并肩?
不。
她不会让她得逞。
过去的伤害已经造成,无法抹去。纠结于这张纸,除了反复撕开自己的伤疤,除了让亲者痛仇者快,没有任何意义!
她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将胸腔里所有的郁结与痛苦都挤压出去。然后,她拿起书桌上的一个古董黄铜打火机。
“咔哒”一声轻响,一簇幽蓝的火苗跳跃起来。
她将那张支票影印件凑近火焰。
橘红色的火舌贪婪地舔舐上纸张的边缘,迅蔓延,吞噬了那令人眩目的金额,吞噬了那力透纸背的签名,也吞噬了那行恶毒的附言。
火光映照着她平静无波的脸庞,那双清澈的眼眸里,倒映着跳跃的火焰,仿佛也有什么在其中被一同燃烧、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