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文学>太子妃他只想搞钱 > 第91章 十 (第1页)
第91章 十 (第1页)
第91章十……
皇帝一连下发了三道旨意,一是圣驾搬回乾清宫,二是解除东宫的禁足,三是命太子离京北上随军作战。
前两道正是朝臣担忧切盼之事,皇帝能回心转意自然皆大欢喜。然而最後一件,又引起不小的轰动。
自古以来,鲜少有储君出征。更不必说眼下皇帝病重,监国之权正由太子掌领,京城岂能群臣无首?
皇帝强撑着精神见了衆位廷臣,表示自己尚能处理要务。又说太子年轻,该去军中历练。
却字句不提星象异动。
然而衆人都清楚,圣旨里头所谓的“随军作战”,几乎是相当于是暂且将太子逐出京城了,言之更甚者,便与充军并无分别。
六科给事中齐齐发威,以强硬的态度封驳中旨,一时竟连内阁都无可奈何。
皇帝对着兰怀恩发脾气:“太子储君的身份摆在那,朕派她去可提振士气;她不领军,无实权,威胁不到京城,也威胁不到边境作战……这是朕能作出的最大让步了,一举数得的事,这群老顽固怎麽还是不知好歹?”
兰怀恩抚着皇帝的背替他顺气,柔声劝道:“朝臣无非就是怕太子有什麽闪失……依臣看,命太子离京就极为合适。左右陛下还在京城坐镇,太子留在京城也是无所事事,不如派去边关,除却那些好处不说,也全了太子那份孝心不是?”
皇帝嗬嗬发笑,睃他一眼:“……朕看那些大臣就是巴不得朕赶紧驾崩,好早些拥立太子。她这些年倒是越来越能干了。”
提起来孝心,皇帝又想起太子写的那封信。入眼一手齐整的小楷,字句谨慎,言辞恳切感人。
彼时他已有派太子离京之意,恰巧一打开信,便看到太子自请出征,并将其中益处面面俱到地分析清楚。他顿时竟深感欣慰。
不得不说,太子在大事上一向拎得清轻重,顾全大局。
“既是太子主动请缨,便让她去应付那些大臣吧。这些天叫你东厂的人警醒着点儿,抓几个兴风作浪的,好好严惩。朕可不是太子,由着他们猖狂。”
兰怀恩应了声是,为皇帝放下帷幔後,又开口请求:“陛下,臣……臣不如跟在太子身边一同去罢,一来臣是御前的人,二来可护太子安危,三来若太子当真有何异动,臣也能及时……”
“你以为朕当真要让她一个人去边关?”皇帝失笑,冷哼一声,“她有侍卫,你去算怎麽回事?再说你走了,东厂司礼监怎麽办,朕身边也离不开你。还有,朕倒还不至于怀疑太子怀疑到让你去贴身监视,把朕当成什麽人了?”
“臣……”
“你去帮着准备太子离京事宜。她第一次上战场,即将面临刀枪剑戟血雨腥风的场面,难免要心慌意乱。”皇帝疲惫地闭上眼,沉沉睡去。
。
既有太子出面解释,衆臣便不得不妥协。
阁臣最先识趣,知晓此事再无转圜的馀地,早早就站到了皇帝和太子这边。少数仍坚持己见的,要麽被东厂挑刺打压,要麽只能将满腔愤懑咽回肚子里。
翰林院编修崔文藻有事上禀,却绕过呈进奏折这一道程序,不经内阁,更不与詹事府沟通,仗着姓崔,径直求到了梁禄跟前。
彼时晏朝才从内校场练完武回宫,浑身汗意尚未褪去,听崔文藻说完,无非还是那几句,不免心烦气躁。
“你这些话本宫听过无数遍了,没什麽新意,也改变不了结果。”
晏朝转过身,看到他神色有些窘迫,便将口吻放缓:“你若想不明白,记着本宫的话就行:陛下与本宫父子一体,陛下所忧即为本宫所想,陛下所愿亦是本宫所盼。如今敌肆猖獗,本宫身为储君,自要为君父分忧,更要有身先士卒之勇。”
崔文藻当即愣在原地,不顾礼仪地擡头直视她。然而晏朝面色如常,只是垂目理一理衣袖,从容静立。
他沉默半晌才仿佛悟出点什麽,深深一揖:“微臣惭愧。今日莽撞之举,还请太子殿下恕罪。”
。
梁禄开始忙碌起来,离宫需要带的物品得他亲自操办。因着晏朝的身份,还有好些东西得万般谨慎,半分马虎不得。
他列了一份详细的单子呈上去给晏朝过目,又请示:“随行人员,还需请殿下指定。”
晏朝一目十行看了眼,颔首道:“经你手你置办的本宫都放心。至于随行人员……首先,你就不必去了吧?”
梁禄怔愣片刻,擡眼望她神色,犹豫半晌还略有些支吾:“奴婢丶奴婢一直是跟着殿下的,您身边若没个可靠的人,奴婢也委实放心不下……”
晏朝轻轻一笑,宽慰他:“这是去打仗,不是寻常外出。你又不上战场,安心留在京城将东宫守好即可。”
梁禄垂首,讷讷低言:“殿下这是嫌弃奴婢老了丶不中用了。”
晏朝轻喟一声,温和摇头:“并不是。本宫身边你最可靠,所以才不能让你身犯险境。你留在京城,便是本宫的一条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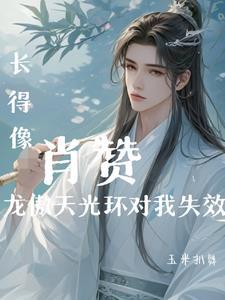
![火葬场渣攻不干了[快穿]+番外](/img/84681.jpg)
![(原神+崩铁同人)[原神+崩铁]魈鸟梦里会遇见元咪吗](/img/6742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