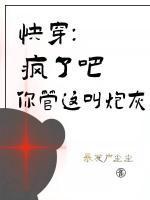少年文学>哑雀无声的反义词 > 孩子们的谢谢(第1页)
孩子们的谢谢(第1页)
孩子们的谢谢
图书馆落成那天,海面上飘着层薄薄的雾,像谁在清晨的窗棂上蒙了层纱。
江熠站在福利院新修的红砖墙外,看着工人把最後一箱绘本搬进去,纸箱上印着林微画的玉兰花瓣,被晨光染成了淡淡的金粉色。
三年前在树洞里捡到的铁盒就放在他随身的帆布包里。盒子里的两颗石头被他摩挲得发亮,一颗是林微被拐时攥着的,边缘带着海水冲刷的圆润;一颗是他在货车厢底摸黑捡到的,棱角还带着点尖锐,像没被岁月磨平的记忆。
“江熠哥,孩子们都等不及啦!”晓棠的声音从铁门里传出来,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清亮。她今天穿了件白色的连衣裙,裙摆上绣着小小的海棠花,是她妹妹出院後亲手缝的——那个和林微一样爱画玉兰的女孩,现在已经能蹦蹦跳跳地跟着哥哥来图书馆帮忙了。
江熠笑了笑,推开那扇刷着新漆的木门。
门轴转动时发出“咯吱”的轻响,像福利院老玉兰树春天抽芽的声音,让他想起很多年前,林微就是这样推着吱呀作响的铁门,举着素描本冲进废弃厕所,用稚嫩的笔触护着他的练习册。
图书馆的挑高很高,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斜斜地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斓的光斑,像林微画过的海边星空。书架是原木色的,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每一层都摆着码得整整齐齐的绘本,书脊上露出各色封面:有《海的女儿》里泡沫般的蓝,有《小王子》里玫瑰色的红,更多的是印着玉兰花瓣的米白——那是他整理出版的林微画集,改了结局的那本。
孩子们已经排好了队,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校服,小脸上带着点拘谨,又藏不住雀跃。
最小的那个扎着羊角辫,发绳是红色的,像极了照片里林微小时候的样子,她手里攥着片玉兰花瓣,大概是从院子里新栽的树上摘的。
“大家安静哦,”晓棠站在临时搭起的小台子上,学着当年林微的样子,指尖轻轻并拢,比了个“安静”的手语,“今天我们要谢谢江熠哥,还有一位……在天上看着我们的姐姐。”
她的声音顿了顿,目光落在最上层书架正中央的那幅画上——林微画的福利院玉兰树,树下两个身影的指尖快要碰到一起,像在传递什麽珍贵的东西。画框是江熠亲手做的,用的是当年从推土机下抢出来的玉兰树枝,木纹里还能隐约看到他小时候刻的“1”和“2”。
江熠走上台,手心有些发潮。他很少在这麽多人面前说话,尤其是在这些眼神清澈的孩子面前,总觉得所有的语言都显得笨拙,不如林微的手语来得直接,不如橘子糖的甜味来得实在。
“这些书……”他开口时,声音比预想中稳些,“有些是别人捐的,有些是我和一位姐姐画的。她总说,书里藏着光,翻页的时候,就能看见想看见的人。”
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眨着眼睛。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举起手,奶声奶气地问:“那姐姐能看见我们吗?她也喜欢橘子糖吗?”
江熠的心轻轻颤了一下。他想起林微最後那封信里说“天上的星星最亮那颗是我”,想起她咳得喘不过气时,还攥着颗没吃完的橘子糖,糖纸在掌心揉成小小的团,像颗不肯熄灭的火星。
“能看见的,”他蹲下来,平视着那个孩子,指尖轻轻碰了碰她手里的玉兰花瓣,“她比谁都喜欢看你们笑,也比谁都喜欢橘子糖的甜。”
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把花瓣小心翼翼地夹进怀里的绘本里,动作像在藏什麽宝贝——和林微把石头塞进他手心时一模一样。
晓棠适时地递过来一个剪彩用的红绸带,绸带两端系着两朵纸做的玉兰花,是孩子们前夜熬夜折的,花瓣上还沾着点胶水的痕迹。“江熠哥,我们剪彩吧?”
江熠接过剪刀,金属的凉意从指尖传来,让他想起多年前警察带走他时,手铐锁住手腕的触感。只是这一次,掌心是暖的,眼前是亮的,不像那天的阳光,明明很烈,却照不进他瞬间冰凉的眼底。
剪刀落下时,红绸带飘落在地,像道被解开的牵绊。孩子们爆发出一阵欢呼,又很快捂住嘴,大概是想起了晓棠教的“安静”,眼底的笑意却藏不住,像盛了满眶的星星。
“现在,可以去选书啦,”江熠拍了拍手,声音里带着点自己都没察觉的温柔,“记得要轻轻翻页,书里的朋友会疼的。”
孩子们像一群刚破壳的小鸡,叽叽喳喳地散开,踮着脚尖在书架前挑选。
有个小男孩指着林微画集里的橘子糖插图,拉着旁边的女孩小声说:“你看,这个糖像不像张阿姨给我们发的?”
女孩点点头,指着两只交叠的手:“他们在分享吗?就像上次你把饼干分我一半。”
江熠站在角落,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眼眶有些发热。他想起林微的素描本里,有幅画是两个小小的身影蹲在玉兰树下,分吃一颗橘子糖,糖纸被风吹得飘起来,像只白色的蝴蝶。旁边写着行小字,是他教她写的:“分着吃,更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