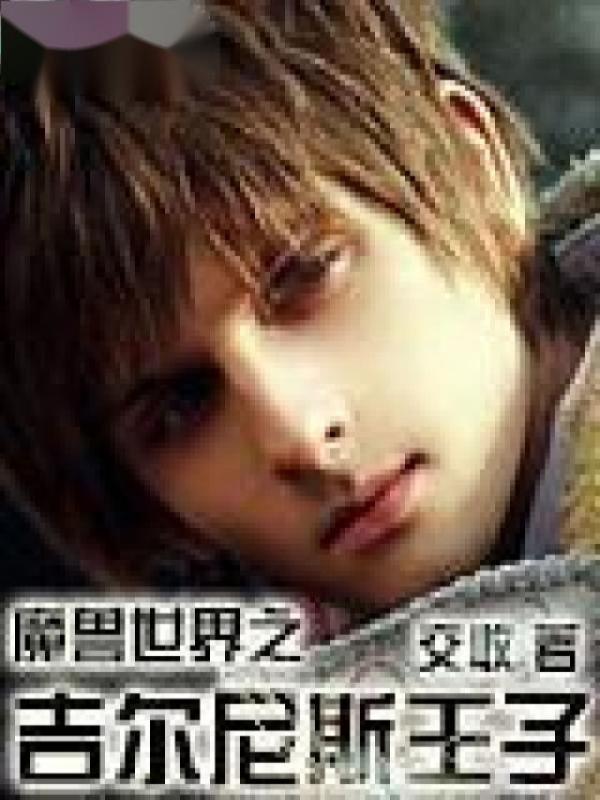少年文学>留白的拼音 > ◇ 第50章 第四十五章 心火(第3页)
◇ 第50章 第四十五章 心火(第3页)
封燃疑心不已:“真的?那快松开我。”
沈执仍微笑着说:“不了吧,省的你哪天又跑。”
“我要跑早跑了,前些天处处都是机会!”
沈执依旧不松口,封燃拿不准他心里想着什麽,一时间焦头烂额,不知怎样才好。
就这样过了一夜,吃喝拉撒都在一张椅子上,中间甚至被按着解决数次需求。封燃身心极受重创,腰酸背痛,双臂沉重如铁,有脱力的前兆。
他有气无力地说:“我说,你要打算来这一出?”
沈执的笔刷间或在巨大画板上描上痕迹。这是他近几个月正在完成的作品,花费相当一番心思,乃止连夜搬离那座小平房,什麽都没带,只带了它。
“哪一出?”听他说话,沈执隔许久才应,接着转动调色盘,落下一笔。
“这一出,”他昏昏欲睡地说,“安全-词是什麽?”
“……”沈执扔掉调色盘,跳下长梯走近,“你从哪知道的这些乱七八糟的?”
“别管。再说我知道的比你多,不很正常吗。”
“你和谁试过?”
“知道就一定试过?”封燃反问,“你不也知道麽,那我能不能这样怀疑你?”
沈执闭口不语。
“难受。”他再次睁开眼睛,一副可怜模样,“手快断了,真的。”
“又不是没放松过。”沈执毫不留情扔下一句。
封燃知道他还在生气,但气什麽,不知道。
交往这些年他早习惯沈执阴晴不定又不肯明说的毛病,多少能猜出个七八成。
而此刻,饶是再有耐性,被如此折辱了一天一夜,也再没法好声好气去哄丶去服软。
他干脆闭嘴,闭目养神,昏昏沉沉地度过一个下午,直到第二个夜晚。
门被风吹打的声音很刺耳,他猛然惊醒,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轻唤了一声沈执。
无人回应。
无边际的恐惧瞬间吞没一切,他开始奋力地挣扎。不远处水声愈发明显,富有节奏,那是浪潮拍打海面的声音——他在海边。
海风骤然剧烈,屋顶咣当作响。接着是豆大雨水。
坏事成双。房顶开始渗水,沿着墙壁,一颗颗落在他身上。
他只穿一件薄衫,雨水刺骨冰冷,凉意逼人。
激烈的挣扎下他带翻了椅子,摔倒在地。额角不知撞到什麽,咸腥液体流入口中,他咬着牙,想一点点脱出绳索。
绳是新系的,沈执很用心,换了种打法。
结灵活如蛇,越用力越禁锢,直到再无一丝丝的动作馀地,手指都胀痛充血,仍牢牢卡住。他只好放弃。
绝望之际他猛然想起,这东西,还是他教沈执的。根本解无可解。
那时是绑重物用,哪知会有今天。
冷静几分,痛感才从各处袭来,雨水伴着冷汗和血液洗刷身体,他倒抽口气。
骤然回忆起这些天的种种,悉心照料的人反过来对他这般折磨,寒气从心口一直穿透到四肢百骸。
或许一个小时,或许半个夜晚,沈执不见踪影,将他扔在漆黑的屋子,动不得,跑不了。
他的心底越发不安,肚子饥饿感明显。自己难不成会死在这里,无人知晓。沈执是不是故意报复,要把他饿死渴死……
又一股更大的风雨袭来,玻璃窗脆生生碎成渣,他狠狠打了个寒战,额角青筋跳动,忍无可忍地发泄出声。
“沈执你真他妈够有种的就别给我回来,你个垃圾,人渣——”
门吱呀一声拉开,沈执一袭素衣站在浓稠的夜色里,如同神祇降临。他长身玉立,海风吹拂额发,仿佛羸弱到站不稳,眼里浪潮翻涌,仍是叫人猜不透,摸不着。
他迈入一步,又停下来。
地上,与木凳紧密相连的人狼狈不堪地喘着粗气,眼底怒意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