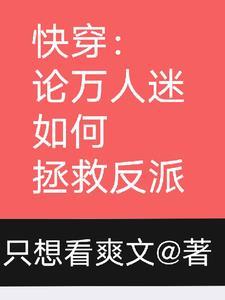少年文学>浓浓烈烈的意思 > 第65章 第 65 章 赶到火光(第1页)
第65章 第 65 章 赶到火光(第1页)
第65章第65章赶到,火光
最後一位香客顶着风雪离去後,清云庵便闭了门。
冬日天短,日头一落,天色便灰蒙低垂。雪花纷纷扬扬飘落,庵外石阶的毡毯上浅浅覆了一层白,不多时,那灰色便尽数没于雪下。
尚书令爱屋及乌,唯恐夫人受寒,不独佛堂厢房,连膳厅,庖厨及下人候令的偏房皆通了地龙,绝称不上怠慢。
然今日终究不同,元日佳节,阖家团圆之时,却教人在此简食等候,庵中师傅们唯恐招待不周。
府上下人却规矩极严,皆自称身卑,膳食茶水皆亲往膳房自取。云亭手捧盛满福袋的漆盘敲门入内,朝衆人念了声佛谒,
“庵中膳食简陋,怠慢之处还望海涵。此乃佛前诵经祝祷过的福袋,可祛秽辟邪,赠予诸位,祈愿福泽相伴。”
府中仆从不论心中作何想,面上皆露受宠若惊之色,连称“有幸”,一一躬身接过。
碧玉上前双手捧接,吩咐青萝与人分发,又转身合十回礼:“奴婢等得此福缘,全赖夫人垂怜,庵中师傅厚爱。惟尽心服侍夫人,以报恩泽。”“阿弥陀佛,施主有心了。”
云亭目含温光,“天寒地冻,贫僧便不多扰了。”
“有劳师傅。”
碧玉送人出门却未折返,迎上对方不解的目光,主动解释道,“夫人心善,许我等半日清闲,然奴婢等岂可视作理所当然?眼下也该至夫人跟前复命侍奉了。”
早在申时,兰浓浓便以无事不需随侍为由,打发碧玉等府中下人至偏房歇息。她平日虽极好说话,然毕竟是主母,身份尊贵,气度天成,稍敛容色时,那三分与大人相似的威仪便压得人不敢妄动。
主尊奴卑,碧玉等人自是恭顺应下,退避歇息。
然时至晚膳,万无奴婢不近前服侍,反自行用膳的道理。
尚书令府规矩体统森严,云亭听闻并无异色,只合十颔首,却驻足低声道:“施主尽职有心,与浓浓倒是主仆同心。方才贫僧来时,浓浓曾有言托付,道若碧玉姑娘未提便罢,若提及近侍之事,便嘱你不必前去,待令公大人到来再行伺候。”
碧玉擡眸望去,清云庵中师傅皆主清修,不慕尘乐,人人皆是一副清淡寡欲之态,也惟有在夫人面前方露几分温情。
“既如此,奴婢谨遵夫人之意,谢夫人体恤。”
廊外雪声簌簌,自後院步入侧院的石径早已被积雪覆盖,蓬松洁白,杳无痕迹。
正厅门未关合,厚帘垂落,自绸窗透出暖黄烛光,谈笑声隐约可闻。
云亭踏上石阶,收伞置于门前架中,整了整衣袖禅袍,拍去寒意,方掀帘而入。
帘隙开合间,屋内语声倏然一静,如沙尘扑火,骤归湮灭。
素净的圆桌上摆了许多平日罕见的膳食甜点,庵中衆人围坐,面上却皆是一片沉寂忧色,偏还要强作轻松,断续说着与神情迥异的闲话。
灯花爆烛,宴时已过半,满桌菜肴几乎未动。云安手捧碗筷,耳中嗡鸣,喉头如堵沙砾,本该出口的话半个字也吐不出。
她低着头,眼前那方特为今日备下的蓝底橙花桌布上,正洇开一团不断扩散的褐色水迹,忙搁下碗筷偏头拭面。
眼下正是寒气最重的时候。浓浓本就冻伤了身子,落下病根,外头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她能否受得住?药效可曾顺利过去?醒来时可会惊慌伤身?她一介女子孤身上路,可能平安?日後可否顺遂?
云安止不住这些纷乱的念头,一时忧她禁不住风雪病势加重,一时又怕她举目无亲孤单害怕,不知能否安然落脚,更恐她突遭不测。
一颗心跳得又急又重,忽又忍不住想,这般不顾她意愿,强行送走,究竟是对是错?
可那人平日将浓浓看得极紧,似今日这般分身乏术,庵中香客络绎之机,实在难逢。
而出其不意,恰是可为之机。
擡头看向庵主,唇齿微动欲言,却又恐隔墙有耳,终是咬牙忍下。
饭桌上听来和乐融融,衆人面色却皆是一片沉寂忧惶。惟清风庵主神情沉静,指间盘着念珠,自袖中取出一张早已备好的纸条,就近递予身侧一人。
她端起碗筷,语气清淡如常:“天寒物易凉,莫要只顾说话。来日方长。”
那纸条上仅书十一个字。她话音落时,衆人已尽阅,惴惴心绪竟真的被悄然抚平。
尽人事,听天命,泰然处之尔。
然矣。既已尽人事,与其杞人忧天,不若为浓浓祈福祝祷。惟愿其安然无恙,馀生尽欢。
---
雪一直下,似是要将前两日未落的份一并补尽。清云庵周遭数里人烟寂寥,夜深雪重,烛影零星。
若在寻常这般天气,唯有风雪的呼哨与木鱼诵经之声交织相应。而今夜,却不闻经声,惟闻欻欻清雪之音不绝于耳。那是尚书令府下人为迎候必将到来的主人,不惧风雪洒扫庭除。
屋中衆人默然端坐,闭目凝神。指间念珠偶有微滞,旋即复常,似已将杂念尽数摒弃。
心静便不觉光阴流转,待风雪悄止,万籁俱寂时,一道脚步声自远而近,不重,却步步匀稳,踏雪而来间尽显权势蕴养的从容。
清风庵主睁目,迎上衆人虽微慌却犹带镇定的面容。她本是庵中性情最寡淡之人,终年神情如冰封静湖,此刻却罕见地和缓了眉目,唇角一点笑意如春冰初泮,竟予人春风拂面之感。
“阿弥陀佛。既来之,则安之。出去吧。”